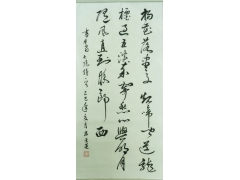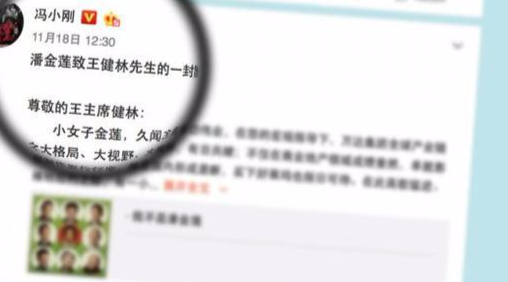
11月18日,冯小刚在微博上以潘金莲的口吻,就其执导的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在万达影城遭遇低排片的事情,向王健林发表了一封公开信。
在众人眼中,西门庆与潘金莲成了“奸夫奸妇”的代名词,冯小刚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中的“潘金莲”也是如此影射。
我们经常听人说,古时捉奸在床,当场杀死无罪。其实,这样的法律规定,只存在于秦汉-魏晋时期,又在元、明、清时恢复,但唐宋法律却无类似的规定。
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,会被浸猪笼吗?
冯小刚撕逼王思聪在网络热炒,顺带也火了一把冯导的最新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拜戏剧、评书、小说、影视作品的传播所赐,西门庆与潘金莲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奸夫奸妇,甚至成了“奸夫奸妇”的代名词,冯小刚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中的“潘金莲”,便是代称。但尽管潘金莲的通奸故事已是家喻户晓,对这通奸故事背后的法律史知识,你却未必了解,也许还会误信传闻。

通奸的罪与罚
我先提问一个问题:如果潘金莲并没毒杀亲夫武大郞,只是与西门庆通奸,那按宋代的法律,会受到什么处罚?
我们看小说、戏剧,总以为古代妇女与人通奸,会被判处什么“骑木驴”、“浸猪笼”之类的酷刑,其实这多出于民间小文人的杜撰。虽然个别地方确实发生过将奸夫奸妇“骑木驴”、“浸猪笼”的事情,但那不过是落后、封闭之地的私刑而已,既为主流社会所反对,也为法律所禁止;国家正刑中从来没有什么“骑木驴”、“浸猪笼”。根据《宋刑统》,“诸奸者,徒一年半;有夫者,徒二年。”通奸的男女将被判处一年半的徒刑,如果女方有丈夫,则徒二年。
但实际执行的处罚,还要更轻一些。因为宋朝创设“折杖法”,除了死刑之外,流刑﹑徒刑﹑杖刑﹑笞刑在实际执行时均折成杖刑。根据宋朝“折杖法”,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,如果没有发生毒杀武大郞的情节,单按通奸罪量刑的话,二人会被判“徒二年”之刑,折脊杖十七,即打脊背各十七下就可释放了。
我再问一个问题:假设武大郞一日回家,发现潘金莲与西门庆正“滚床单”,他一怒之下,当场杀了奸夫淫妇。武大郞用不用对此负刑事责任?
我们经常听人说,古时捉奸在床,当场杀死无罪。其实,这样的法律规定,只存在于秦汉-魏晋时期,又在元、明、清时恢复,如元朝的律法规定,“诸夫获妻奸,妻拒捕,杀之无罪。……诸妻妾与人奸,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,……并不坐。”明清刑律也规定,“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,登时杀死者勿论,若只杀死奸夫者,奸妇依律断罪,当官价卖,身价入官。”这样的立法,无异于赤裸裸鼓励亲夫将通奸的奸夫与奸妇一并杀死。
但是,唐宋法律却无类似的规定。换言之,在武大郞生活的宋代,国家法律并不承认亲夫有什么“捉奸在床、当场杀死”的权利。假设武大郞杀了奸夫奸妇,就必须负杀人的刑事责任。
我接着再问一个问题:发现西门庆与潘金莲有奸情的小郓哥,能不能跑到衙门去检举,然后衙门捉住奸夫奸妇治罪。

根据宋朝的立法,小郓哥不具有诉权,即使跑去检控了,衙门也不会受理。因为宋朝法律规定“奸从夫捕”。什么意思呢?意思是说,妇女与他人通奸,法院要不要立案,以妇女之丈夫的意见为准。从表面看,这一立法似乎是在强调夫权,实际上却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益的保护,以免女性被外人控告犯奸。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: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属于亲告罪,受害人(丈夫)亲告乃论,政府与其他人都没有诉权。
元朝时,“奸从夫捕”的旧法被宣布作废,元廷颁下新法: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,准许捉奸,“许诸人首捉到官,取问明白”,本夫、奸妇、奸夫同杖八十七下,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。从此,人民群众心底的“捉奸精神”被激发了出来,涌现了很多被坊间小文人津津乐道的捉奸故事。

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剧照。(电影剧照/图)
“奸从夫捕”的立法意图
宋代的“奸从夫捕”立法,其实是一条良法,被元人废除了非常可惜。为什么说它是良法呢,我讲一个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收录的故事你就理解了。
大约宋宁宗时,广南西路永福县发生一起通奸案。教书先生黄渐,原为临桂县人,为讨生活,寓居于永福县,给当地富户陶岑的孩子当私塾老师,借以养家糊口。黄渐生活清贫,没有住房,只好带着妻子阿朱寄宿在陶岑家中。
有一个法号妙成的和尚,与陶岑常有来往,不知怎么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。后来,陶岑与妙成发生纠纷,闹上法庭,陶岑随便告发了妙成与阿朱通奸的隐情。县官命县尉司处理这一起通奸案。县尉司将黄渐、阿朱夫妇勾摄来,并判妙成、陶岑、黄渐三人“各杖六十”,阿朱免于杖责,押下军寨射充军妻。
这一判决,于法无据,于理不合,完全就是胡闹。
黄渐当然不服,到上级法院申诉。案子上诉至广南西路提刑司,提刑官范应铃推翻了一审判决。在终审判决书上,范应铃先回顾了国家立法的宗旨:“祖宗立法,参之情理,无不曲尽。傥拂乎情,违乎理,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。”然后指出,阿朱案一审判决,“非谬而何?守令亲民,动当执法,舍法而参用己意,民何所凭”?而且,县司受理阿朱一案,长官没有亲审,而交付给没有司法权的县尉,“俱为违法”。
最后,范应铃参酌法意人情,作出裁决:“在法:诸犯奸,许从夫捕。又法:诸妻犯奸,愿与不愿听离,从夫意”,本案中,阿朱就算真的与和尚妙成有奸,但既然其夫黄渐不曾告诉,县衙就不应该受理;黄渐也未提出离婚,法庭却将阿朱判给军寨射充军妻,更是荒唐。因此,本司判阿朱交付本夫黄渐领回,离开永福县;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,却犯下通奸罪,罪加一等,“押下灵川交管”,押送灵川县看管;一审法吏张荫、刘松胡乱断案,各杖一百。
范应铃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,他的判决书申明了“奸从夫捕”的立法深意:“捕必从夫,法有深意”,“若事之暧昧,奸不因夫告而坐罪,不由夫愿而从离,开告讦之门,成罗织之狱,则今之妇人,其不免于射者(指奸妇被法院强制许配为军妻)过半矣”。如果男女之间一有暧昧之事,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,便被人告到官府,被有司治以通奸罪,则难免“开告讦之门,成罗织之狱”。因此,国家立法惩戒通奸罪,又不能不以“奸从夫捕”之法加以补救,将通奸罪限定为“亲不告官不理”的亲告罪,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。
那么,“奸从夫捕”的立法,又会不会给男人滥用诉权、诬告妻子大开方便之门呢?应该说,不管是从理论,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,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。不过,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收录的另一个判例显示,宋朝法官在司法过程中,已经注意到防范男性滥用“奸从夫捕”的诉权。
宋理宗时,有一个叫江滨臾的平民,因为妻子虞氏得罪他母亲,意欲休掉虞氏,便寻了个理由,将妻子告上法庭,“而所诉之事,又是与人私通”。法官胡颖受理了此案,并判江虞二人离婚,因为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,“有何面目复归其家”?肯定无法再与丈夫、家婆相处。虞氏自己也“自称情义有亏,不愿复合,官司难以强之,合与听离”。
但是,胡颖同时又反驳了通奸的指控,并惩罚了原告江滨臾:“在法,奸从夫捕,谓其形状显著,有可捕之人。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,诬执其妻,使官司何从为据?”判处江滨臾“勘杖八十”,即杖八十,缓期执行。
从法官胡颖的判决,我们不难看出,宋时,丈夫要起诉妻子犯奸,必须有确凿的证据,有明确的奸夫,“形状显著,有可捕之人”。这一起诉门槛,应该可以将大部分诬告挡之法庭门外。
很多文明体都设有通奸罪
看到这里,也许你还会反驳我:不要给宋朝的通奸罪立法“洗地”了,真正文明的社会根本不会设立什么通奸罪,只有中国古代与那些落后国家才会将通奸行为入罪。
我不能不说,这是你的想当然。实际上,不少西方国家直到完成近代化之后,仍然在刑法上保留着通奸罪,如1968年《意大利刑法》第五百六十条即规定了通奸罪;1971年《西班牙刑法》编有“通奸罪”一章,通奸男女均处短期徒刑六个月至六年;1994年《法国刑法典》规定,强奸以外的性侵犯罪,处五年监禁并科罚金,这主要针对的就是通奸行为;美国的一部分州至今也保留着通奸罪。
韩国的刑法典也有通奸罪的条款,直到2015年才宣传废除这一条款;中国香港特区尽管未设通奸罪,但在民法上,允许离婚诉讼的一方,将奸夫与奸妇列为共同被告,向其请求损害赔偿;台湾地区现行刑法更是明确规定:“有配偶而与他人通奸者,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其相奸者亦同。”同宋代一样,通奸罪在今日台湾也是亲告罪,“告诉乃论,配偶纵容或宥恕者,不得告诉。”
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,几乎所有的文明体都将通奸行为列为法律明文禁止的罪行,在文明早期,通奸罪往往都被当成必须处死的重罪,如《汉谟拉比法典》规定将与人通奸的女性投河接受神判,古希伯来《摩西法典》对和奸罪处以绞刑、石刑与火刑,古印度《摩奴法典》对已婚妇女的通奸行为处以残忍的兽刑。随着文明的演进,进入近代文明形态,通奸罪呈现出轻罪化的明显趋势,从处死刑演变成只判轻刑,从公诉罪演变成亲诉罪,乃至于只是在刑法上保留罪名,而在司法中基本不予启用。
从中国历史看,通奸行为的罪罚演变呈现为一个U形轨迹:前期(秦汉-魏晋)重罪化,中期(唐宋)轻罪化,后期(元明清)又重罪化。相对而言,宋代法律对于通奸罪的处分,可以说是最为接近现代文明的。